意大利文版《波德莱尔》导言
阿甘本
译者按:本文是阿甘本2012年为意大利文版《波德莱尔: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所撰写的前言。
瓦尔特·本雅明的《波德莱尔: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是一本很特别的书,不仅是因为他那非比寻常的形式,而且也因为它那带有冒险风格的历史故事,或者毋宁说,一种前历史,至少对我来说,这个前历史与印刷文献形式的存在密不可分。
1981年,那时我在巴黎,在那里寻找一些著名文献的踪迹,按照丽萨·费特科(Lisa Fittko)的说法——就是这个女人,帮助本雅明从被纳粹占领的法国逃亡到西班牙,最终本雅明在那里终结了自己的生命——本雅明将这本文献收藏在他的一个黑色皮套的文件夹里。
因此,我翻阅了全部乔治·巴塔耶的通信集,那时,这些通信集还收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手稿部里。想象一下,当我发现了一封巴塔耶写给让·布鲁诺(Jean Bruno,当时图书馆的一名图书管理员)的信件,在信中,巴塔耶叮嘱布鲁诺要好生照看这些本雅明托付给他的非同一般的手稿时,我当时是多么的震惊和惊喜。顺着这封信读下去,布鲁诺做了一个批注:"这些手稿现在被收藏在B.N.柜"。信的日期与批注的日期不同,但两个日期都晚于1947年,也就是巴塔耶将这些手稿的所有权交付给了皮耶尔·米萨克(Pierre Missac),而后者将这些手稿交给了阿多诺。
我迅速冲到手稿室的管理员那里,并问她是否了解这些手稿在哪里。她断然否定了图书馆收藏过任何本雅明的手稿,但面对这样一个批注的证据,他同意打电话给布鲁诺,那时布鲁诺已经退休了。布鲁诺不太记得这些手稿的情况,但他十分确定,如果他批注过手稿在图书馆,那么这必定确凿无疑。
随后,图书管理员开始寻找部分手稿的工作,一个月之后,我收到了她一条简短的来信,信中告诉我手稿找到了,我可以过去了解一下。我被告知,这些手稿的确保存在图书馆,但巴塔耶的遗孀并未捐献出来,而图书馆不会为没有所有权的手稿编目。我被带进一个房间,那里有一个木制的柜子,收藏着这些保存的手稿,其中还囊括一些其他重要作者的手稿,或许这些手稿都有待编目。
无论如何,我从图书管理员那里收到了五封黄皮纸信封包裹着的本雅明的手稿(其中一些是打印稿,但其中绝大部分是我相当熟悉的手写字体的稿件)并非毫无感觉。这不是我第一次对发现本雅明的手稿感到如痴如醉。当我们研究一个作者并沉浸在他的思想、他的著作、他的生命中时,会发生某种很奇怪的现象,这种现象有点像是着了魔法,但我相信这种魔法可以归结为吉奥达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所说的"自然魔法",而他认为自然魔法是一种特殊的物质科学。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真的认同一位作者的精神,用文献学的热情去思考和研究他的作品,他的字眼,如果,正如在我这里,你多次到达他生活过的和他与其他人交谈过的地方,所以,如果你与他发生接触,也就是说,接触到这些材料,发生了某种预想不到的交流(correspondence, 在隐微教诲的意义上,correspondence已经出现在波德莱尔那里,本雅明很小心谨慎地评注了波德莱尔的谈correpondence的诗)。这种交流早些年出现在我在罗马的时期,那时,我从家里(我家那时住在鲜花广场(Campo dei Fiori))发现了足足300英尺厚的材料,我家的房子是赫伯特·布鲁门塔尔·贝尔莫尔(Herbert BlumenthalBelmore)住过的房子,他是青年本雅明在1914年到1916年柏林期间最要好的朋友之一。本雅明后来与他割席断交,但他保存了一大批本雅明的信件和手稿,他现在把这些手稿移交给我,现在我仍然拥有着这些手稿。最好玩的事情是,当他向我展示这些他精心保存的手稿时,他也同时向我承认,他很讨厌这位作者,他与本雅明已经六十年没有见面了,而他不知道本雅明已经去世四十年了。就好像波德莱尔之前非常熟悉后来突然绝交的一位对手一样,在感情上伤害了他,因爱成恨。
好吧,回来谈谈巴黎手稿。发现这些手稿非常重要,因为这些手稿让我们看到了本雅明一生最后三年(即1937年到1940年)里的著作的样貌。实际上,其中一个信封包括了一系列本雅明参考了论波德莱尔的书籍,在《拱廊计划》写作的间歇,本雅明绝大多数时间都在看这些书。
1937年3月,本雅明完成了他论福克斯(Fuchs)的手稿,这是给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下一本著作的三个可能的主题之一。第一个主题是论克拉格和荣格,试图澄清他关于《拱廊计划》的方法论问题,而他已经为此工作了若干年;第二个主题是"资产阶级历史编年和唯物主义历史编年之间的比较",与第一个主题很类似,目的是确定一个全书的概念框架,"最后,如果你们不同意我的这种研究方式……我会建议你们,直接进入主题,即直接看关于波德莱尔的部分"。本雅明的第一个主题遭到了拒绝,在社会研究所那里,意味着他与弗洛姆在精神分析问题上产生了激烈的争论,第二个主题,与"福克斯"部分所处理过的问题过于重合,而第三个主题引起了霍克海默的重视:"这就是长期以来所希望的从唯物主义角度来研究波德莱尔的文章。如果你能够首先写出你的著作的这一章的话,我将由衷地向你表示感谢。"
几个月之后,在克服了多次更换驻地的的困难之后,本雅明开始了他的写作。
在这个阶段,无论对于其客户(社会研究所)还是对于作者乱说,这个计划都是正在进展中的本雅明的著作《巴黎,十九世纪的首都》(在与一些信件和朋友交流时,这本书都被非正式地叫做《拱廊计划》)一书中的一个章节。被公开的作品,于1935年5月被提交给社会研究所的朋友(那时,他们还在日内瓦,名字叫"社会研究国际协会"(Société internationalede recherches sociales)),里面包括一个部分(即第五章,标题是"波德莱尔或巴黎街道")里面提到一些观念都是这一章原来的看法。然而,随着对材料研究和阐释的进展,本雅明意识到这个计划中的"章节"正越来越重要,且篇幅也越来越厚,而之前他部分预料到了这一点。1938年4月16日,在写给霍克海默的一封信中,他将这部作品分为三个部分,并用了三个词来表达这部作品。
结果是这篇文章篇幅越来越大,而《拱廊计划》的核心主题已经囊括在其中了。这既是由于主题的本质,也是由于本章节的事实,即它就是本书的一个中心章节,反而它需要首先写出来。我已经预料到这种趋势,在于泰迪(Teddie)的交谈中,我将这一章概括为本书的缩编版(Miniaturmmodell)。因为比起我的想法,桑·雷默(San Remo)已经更认可了这一点……波洛克(Pollock)先生要求就上面的问题与他联系,因为之前您所期望的是一篇普通篇幅的稿子。我知道的,但我想,如果我的研究可能成为相当大的篇幅的作品,那样可能会更好一些。我今天仍然希望在原则上不会提出根本性的反对意见,事实上,我真的不知道如何在三四十页的篇幅里怎样处理这个问题最基本的方面。我相反想用更大的篇幅——我指的是用一本书的篇幅——这等于是原来的三倍篇幅,在最低层次上相当于原来的两倍(GB, 6:64-65)。
必须要总结一下,本雅明在这里将《波德莱尔》一书定性为"缩编版"的状况。他确定了部分与整体之间的悖论式关系,其中如果整体包含自身,也就是说,套层结构(en abîme),则部分倾向于与整体结合,充当一个腐蚀性的因素,渐渐地掏空了这部广泛性的著作。再说一遍,在一封7月9日写给肖勒姆的信中,那时本雅明和布莱希特在丹麦,本雅明说他的著作是"《拱廊计划》更精准的版本,他将思想者的整本书和最后的研究都置于运动之中。"(GB, 6:131)。而几天之前,在写给波洛克的信中,他谈到他正在写的这本书是"《拱廊计划》的扩展版","这本书可以从视角上瞥见十九世纪的纵深。" (GB, 6:133)
一个月之后,本雅明已经重新组织了这本著作的材料和结构,他不得不承认,到现在为止,这本"缩编版"已经成为了自动生成的书,这本书逐渐自己囊括了他为《拱廊计划》准备的大部分材料和看法:
我不得不联系霍克海默先生,当这本书对我长期以来已经收集的各种材料进行重新考究的时候,霍克海默先生对《波德莱尔》一书的热情,已经变成了我对这本书的热情。我必须让我自己面对内在于这件事本身之中的必要工作,其结果是,很多东西根本不是我起初想象的那样……这本书不同于《拱廊计划》。然而,这本书不仅包含了很大一部分我为写作《拱廊计划》而准备的材料,而且也包含了后者大量的哲学性内容(GB, 6:158-159)。
8月3日,在一封信中,本雅明再次阐明了这本书的三个部分的结构,在他的批判实验室里,这本书不断增加的体量也在此被重新提及:
很明显,相对于《拱廊计划》的研究与反思,"波德莱尔"章必须单独拿出来考量……《拱廊计划》的基本范畴,即集中讨论了商品拜物教的特征,则完全在"波德莱尔"章得到了体现。尽管我很想限制它,但这部分的进展超出了我研究限定的范围(GB, 6:149)
9月28日,在写给霍克海默的信中(信里还给出了这本书最后一部分的内容,与想象的三个部分的第二部分相对应,其标题是"波德莱尔笔下的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Das Paris des SecondEmpire bei Baudelaire)),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个自动推进的章节,同时还有它与《拱廊计划》之间的关系:
我想以明晰的方式,让本书呈现出《拱廊计划》中的一些最关键的哲学要素。如果在这个原始计划之外,还有一个可以见到的主题的话,毫无疑问,这个主题就是波德莱尔。最终,《拱廊计划》的主要材料和构成要素已经自动地围绕着这个主题而推进了。(GB, 6:162)
通过这种方式,波德莱尔章实际上在原则上消解了关于巴黎的书的整个结构,本雅明也在如下文字中暗示了这个事实:"我将要展开《拱廊计划》的波德莱尔章,而为《拱廊计划》的另外两个章节也在准备中,即论格兰维尔(Grandville)的章节和论奥斯曼(Haussmann)的章节" (GB, 6:163)。
社会研究所不太喜欢这个部分的研究,而在本雅明与阿多诺密集通信之后,开启了这本著作的新的阶段。尽管感到不舒服("我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下生活和工作,这种隔绝状态产生了一种异常的依赖,即依赖于有人能喜欢我所做的事情"(GB, 6:217)),但本雅明直接策划了对研究的第二章的修订版("游荡"( Flâneur)),并按照新的范畴重新整理了材料。6月26日,在给格雷太尔·阿多诺(GretelAdorno)的一封信中,他意识到,在整个生产中,新稿子意味着进一步强化了《波德莱尔》的重要性:"我认为之前从来没有一篇稿子会确定有这样一个消逝点,在这个点上(正如现在它对我来说),从一个分叉点出来的所有我的思考都和谐一致了。"(GB, 6:308)
新稿子(与此前稿子的第二章相对应,而新稿子覆盖了全书的第二章的核心部分)终于在1939年的7月底完成,这一次,远在纽约的朋友表示了热忱的欢迎。现在,这本书比《拱廊计划》更加贴近本雅明理论工作的中心,而1940年的前几个月里撰写完成的《历史概念论纲》似乎证明了这一点,在其作者看来,这本书不是自动推进的文章,而毋宁是"波德莱尔第二次研究的理论中枢" (GB, 6:308),"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文本具有实验性质",在一个月之后在他写给格雷太尔·阿多诺的信中写道,"这些文本不仅从方法论角度起到了为继续《波德莱尔》的准备的作用。"(GB, 6:436)
从论巴黎艺术的"缩微版"开始,《波德莱尔》一书已经具有了"十九世纪原历史"计划的地位——起初这个地位是赋予《拱廊计划》的——这个计划也得到最先进的实现,在这本书里,凝聚着本雅明思想的所有主旨。在1940年5月7日的一封信中,本雅明最后一次提到这本书,几周前,他先从巴黎飞往卢尔德(Lourdes)和马赛,之后偷渡穿过法国-西班牙边界,最后于1940年9月26日死在了波尔特沃(PortBou)。
《拱廊计划》——或者说,本雅明收集的各类卡片和材料,这些东西构成了这本书的文献基础(因为在今天,我们知道编辑给出的《拱廊计划》一书就是本雅明的卡片索引)——由罗尔夫·提德曼(Rolf Tiedemann)于1982年公开出版了,成为了《本雅明文集》(GesammeltSchriften)第五卷。而关于波德莱尔的著作的两个部分已经成稿,反而放在了《本雅明文集》的第一卷里,即三个部分的第二部分的第一稿(《波德莱尔笔下的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以及同一个部分的第二稿(《论波德莱尔的几个问题》(Übereinige Motive bei Baudelaire)),这些已经加上了《中央公园》(Zentralpark)笔记,更多附加的不同性质的材料出版在第一卷的"评注"(Anmerkungen)中。重写这样一本书,以及让这个版本的《拱廊计划》登上舞台,这些东西都没有可能出现了。
随着1981年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发现的这些材料,情况瞬间扭转。其中的一个信封(被发现者编号为第五封)包含了一堆卡片和笔记,这些卡片和笔记都以不同方式指向了关于波德莱尔的著作,(结合在他们帮助下找到的一些手稿一起看)不仅可以让我们以最接近的方式来重构这本书,而且也展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既有整个书的缘起和进展,还有在更一般意义上本雅明这本生前最后的著作的整个研究方法。提德曼毫无疑问是本雅明手稿的最大权威,在出版《本雅明文集》的巴黎手稿选辑时,写到:"如果有朝一日编辑能得到这些手稿,或许有可能在这里(即对于论波德莱尔这本书)……至少可以弄出本雅明的考察的历史评笺本,即便那时可以打破现在的文集版的编辑结构。"(GS,7.2:736)。
现在这本书(中译注:阿甘本指的是意大利文版的本雅明的《波德莱尔》)给出的并不是这样一本历史评笺本(在翻译上,我们完全无法想象弄出这样的版本),而是一个历史溯源版,在今天可能获得的文献基础上,可以让我们在本雅明写作的不同阶段,跟随着这本"创作中"的稿子大量意料之外的相当丰富的材料,以及关系本书缘起和发展的非常清楚的层次,在某种意义上,这构成了对本雅明晚期创作的总结。
我强调"创作中"这个表达,不仅是因为这本书是一种相当罕见的情况,即我们可以成功看到和展现出著作的最初的梗概和重新安排卡片摘录,到最后成书的整个发生的过程。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还因为这本书可以让我们用一种十分典型的方式反思了"创作中"意味着什么——即提出这样的问题:创作中的著作走向何方?或者换个问法,一本未完成的著作是什么著作,以及它与完成了的著作的区别是什么?
我们十分熟悉在这两个概念之间做出清晰的区分,当然,普通的编辑践行着这个区分,让这个区分看似是自明的区分。但事情并不这么简单。有些著作自身就展现为未完成的著作,但是作者依然就像这样出版著作。典型的例子是帕索里尼的《石油》(Petrolio),当然,区分完成的著作和未完成的著作并不容易。如果我们从时间上回溯一下,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著作,不仅仅是文学著作,可以说,是被其他作者完成的(看一下《玫瑰传奇》(Romande la rose)是一个作者开的头,即纪尧姆·德洛里斯(Guillaumede Lorris),但又是另一个作者完成的,即让·德·莫恩(Jeande Meun)完成,贝利尼的名画《诸神的午餐》(Festinodegli)最后是由提香完成的——但这里"完成"一词意思是什么?)
正如区分遗作中的完成与未完成的著作遇到的困难一样,本雅明绝大多数著作都属于这种类型。在这里,做出判定的是出版社,而他们的判定未必依据文献学标准。
事实上,所有的著作都是创作中的著作,在途中的著作:但是通往何处?如果认为著作走向完成的形式,就有点太想当然了。要么达到完成,要么在中途迷失,仿佛道路必然在中途和终点之间。当某些作品——或许所有带有一定分量的作品——都注定是在途中的作品,在指向自身的途中,指向自身并不意味着走向终点,事实上,它多次排斥了终点。正如亚里士多德谈自然时说,所有的工作都是一条道路(hodos),一条指向自己的道路。
在这个意义上,作品会不停地走在这条通往自身的道路上:碰巧,出于各种各样的理由,在某个时刻,作者放弃了工作,如贾科梅蒂(Giacometti)谈他的画作一样。这种放弃并不一定与那些被正当地视为完成的作品完全一致——即便形容词"未完成的"似乎并不足以解释这两种情况。
在这里,我请你们注意一个特别的情况,这个情况说明,甚至文本批评和文献学——即所谓的轶闻学,与编辑文本相关联——正在逐步意识到这个真相。你们知道,在文献学传统中,文献学家的贡献在于考察原稿或现存作品的版本,目的是构成一个版本,即评笺本,而这个本子被视为尽可能最权威的版本。所以在五十年代,贝斯内(Beissner)编辑的荷尔德林圣歌集,成为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评笺版本,在这个本子里,原稿展现了同一首圣歌的若干个版本。但几十年之后,在萨特勒(Sattler)编辑的本子中,圣歌不再是一首圣歌,而是三首、五首、甚至六首圣歌,这些圣歌不再视为是同一圣歌的若干版本或变体,而是各自独立成诗的诗歌,相对于这些诗歌,不再去追问,这首诗是完成了,还是未完成。
这或许对应了我们时代里正在发生的作品概念的危机,在这场危机中,当代艺术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对于其方式,不好专门作出回应。但是,这并非让这个当然至关重要问题向前走。对我来说,最关键的毋宁是向你标示出这个版本的特殊性,或许这个版本第一次以这样的精确度,跟随着作品走向自身。
如果谈及本雅明,这些情况会更为宝贵,他经常在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里与朋友们一起聊起他作品的理论前设,与之相反,他似乎更喜欢将他实质性的创作过程隐藏起来,真实创作,在一些批评者和他的朋友看来,会伤害到他隐微教诲的传奇色彩。或许正是由于这些材料让我们可以用极其清晰的方式了解这本关于波德莱尔的著作缘起和发展的各个阶段,所以打破了这个神话,相反,在这本书的发展过程中,展现了一种本雅明所理解的唯物主义写作的模式,在这样的模式中,不仅理论阐明了创作的物质过程,而且后者也将一束新的光线射向了理论。
本雅明很早就在他著作的文献收集和作品架构上做出了区分。埃斯帕纳(Espagne)和维尔内(Werner)要我们注意这个区分,他们正确地看到,这些东西不能立即为"作品在时间顺序上的两个阶段的区分,从时间顺序上来看,这两个部分是平行的"。事实是,本雅明十分完美地理解了马克思在研究方法(Forschungsweise)和写作方式(Darstellungsweise)之间的区分,而他在《拱廊计划》的第N部分解释了这个区分:
研究必须适应于特殊的材料,必须分析它们不同的发展形式(Entwicklungsformen),并回溯到内在线索(inneresBand)。只有在这个作品完成之后,才能以恰当的方式来再现这个真实的运动。如果这成功了,如果材料的生命(das Leben des Stoffs)现在将自己展现为一种理想的反思,那么看起来我们就不得不去面对这样一个先天的架构。(GS,5.1:581)
为了正确分析智力劳动的过程,我们要好好分析这段话:研究所搜集的材料,并不是某种静态的东西,而有生命的物质,它自身中已经包含了作品发展的形式和内在线索。研究的任务就是要揭示这些形式与线索,让材料的生命最后能以先天架构的形式显现出来。在1935年10月9日写给格雷太尔·阿多诺的一封信中,本雅明写到,他已经将自己推至"一个逐步完成整个作品架构的关键点上,也就是说,那些文献编录所切分开来的关键点" (GB, 6:170-171),他用画图的方式表达了这个区分,与此同时,他也直接解释了文献编录和作品结构,研究模式和写作模式。从文献编录和写作架构的关系来说,这里出现的某种东西很类似于本雅明遭遇在过去与当下之间的"可认识的现在"时描述的东西(Jetzt derErkennbarkeit,这是本雅明最隐秘的概念之一,他自己也承认,"这是按隐微教诲的方式弄出来的概念"(GB, 6:171),但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概念变得完全清晰可见了):
图像的历史索引事实上意味着,它们不仅仅属于某个确定时代,而且首先只能在某个确定时代里,才能解读它们。准确来说,让它们"可以理解"的东西正是其中一个确定的批评点。所有的当下都是有与之同时代的图像所确定的:每一个"现在"(Jetzt)都是一个确定的可认识的"现在"。在这个"现在"之中,真理承载着时间,直至最终湮灭……并不是过去将光线投向当下,或者当下将光线投向过去,而是图像就是这样,在图像中,曾经的存在在一道闪电中,与星丛之中的"现在"结合起来。换句话说,图像就是一个静止点上的辩证法(GS, 5.1:577-578)。
比起以往任何时候来说,在这种情况下,对本雅明具体创作过程的分析,让我们可以澄清他的认识论的基本范畴:正如建构性要素并不是先天性地施加在文献收集材料之上,而是从其自身的内在运动中崛起的,这个运动在不同阶段上逐渐展开,直至最终成稿,因此,当代性(Jetztzeit)并非在时间上只能从当下来界定的东西,它却是一种星丛,在星丛中,在一道闪电中,它与"现在"结合起来,与一个确定的历史事实结合起来,而星丛被两极化为前历史和后历史(参看GS, 5.1:69; N7a,1)。
一个偶然事件或许是历史-哲学文学史上的一个独一无二的事件(当然,这个事件就在本雅明的作品中),由于巴黎手稿(主要是《单目》和《蓝纸稿》的发现,分别对应于意大利文版的《波德莱尔》的2.7和3.3)的发现,让其成为可能,在非常接近的层次上,跟随着它的"内在运动",借助这种方式,在逐渐成稿的过程中,文献编录与"逐步完善"的作品结构产生了交集。
在有了作者的卡片索引(在这里,就是论巴黎的著作的"材料注释"部分)和由它而产生的作品(或者毋宁说,部分作品)之外,在这个奇迹的带动下,我们可以看到卡片索引是面向成稿来变动和安排自身的,让其推进的内在线索昭然若揭。材料的变动在理论上并非中立的,而是伴随着(我们完没有可能判定,在何种程度上,理论反思可以让卡片索引发生变化,或者相反,材料的生命就是理论最隐秘的宝藏)必不可少的哲学方法论部分的创作(其中,《中央公园》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在文本的秩序和布局上,这些哲学方法论的部分就像症候一样,总是交织着元文本注解)。
在古典修辞学那里,介于发现(inventio,今天,我们会说发现主题及其文献编录)和说出(elocutio,对应于写作或成稿)之间,即布局(dispositio),西塞罗将其界定为"按顺序来布置所发现的东西"(rerum iventarum inordinem distributio),这样,布局在本雅明创作进程中出现在前景位置上,明显对立于现代作者赋予优先地位的写作阶段,其特征非常怪异,我们可以正确地称之为"辩证式本雅明布局"。
这也让我们可以从一个恰当的角度来界定"文学蒙太奇",本雅明曾将其作为其作品最恰当的方法(GS, 5.1:574)。正如阿多诺强调说,问题并不在于"仅仅借助于材料的那令人震惊的蒙太奇拼贴(schokhafte Montage)来产生意义",也不在于写一本"只有引文构成的书"。,而是在于——通过写作过程中的中心布局——让蕴含在文献学材料中的发展形式和内在线索,仅仅通过其架构来引导它们走向成稿。从这一点来看,正如提德曼所说,波德莱尔一书肯定让我们认为,"(《拱廊计划》)本雅明并未成稿,但看起来好像完稿了。"(GS,5.2:1073)
在更一般的意义上,关于《波德莱尔》第一稿在信件往来时,本雅明与阿多诺在方法论上的争论,再一次在精神上清楚地说明了(正如这个版本允许我们这样来做)本雅明的写作方法和隐含在写作中的架构性的概念。为了反对他的朋友指责他忘记从理论上来思考问题,于是,这本书陷入了"糟糕透顶的纯粹事实的罗列"(GS,1.3:1098)。本雅明坚持认为这是必要的,而这就是暗含在其架构下的"方法论上的谨慎":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并不是必须去穿戴上隐微教诲的蜡制的翅膀,而是唯有去探索仅仅暗藏在架构之中的强有力的源泉时,我们这种大胆的飞翔才有可能获得成功。在架构上需要在本书的第二部分安排一些在本质上不同于文献学材料的东西。因此,与其说这是一种"苦行式的戒律",不如说这是方法论上的谨慎……当你说这是"糟糕透顶的纯粹事实的罗列"时,你用这种方式概括出来是的真正文献学的态度。必须采用这样的方式,不仅是因为我喜欢这样的结果,而且也就是这样……所展现的有限的事实,与文献学紧密相关,并对研究者施了魔咒,这些有限事实在某个点上消失了,即这些对象都是在一个历史视角下被建构起来的。这个架构的飞行线汇集在他们自己的历史经验当中。这个对象被建构为一个单子。在这个单子这里,正如文本上的证据一样,在僵化的神话中一直沉寂着,而此刻开始具有了生命活力。(GS, 1.3:1103-1104)
在这里需要从字面上来理解他对莱布尼茨的单子论的参照。单子没有窗户,"如有窗户,一切东西都可以进入到单子里,或从单子里逃出去",这意味着单子的变化"源自于内在原则"。另一方面,因为单子的本质是"代表性"的,每一个单子,都连同整个宇宙一起,代表着"分配给它的特殊的物体"。这个文献的哲学证据表明在架构上,它是一个单子,那么这意味着为了可以被解释,它并不需要任何理论的中介性影响,相反,唯有当文献编录和创作架构有所交织,并走向结束的时候,那么作品才能"被解释所侵入,几乎等于是说被解释所震动"(GS, 1.3:1104)。
在本雅明的方法中,复活了中世纪的教义,在这些教义里,材料已经在自身中包含了形式,它已经以"初始"状态和潜在状态包含了形式,认识就是揭示(eductio)隐含(inditae)在这些材料中的形式。对阿多诺来说,直到最后,其中都包含着某种非辩证的残余物,而这种残余物反而是极其深刻的架构,它与材料中的"流体形式"(forma fluens,中世纪的说法)紧密相关。然而,正如中世纪神学家们所说,在架构上不断生成的形式-材料所指向的消失点,并不是神的智慧,而是"我们自己的历史经验"。
实际上也就是说,这里我们看到了作为神话实践的文献学概念,而这就是青年本雅明与肖勒姆所讨论的问题。正如在所有的神话经验中,文献学家不得不拉低自己的身体和灵魂,屈就于文献、档案和注解,誊写版和各种版本当中那些含混和迷雾重重的研究。但是这种实践的风险在于,会经常迷失自己的道路,但它与材料有着亲密的接触,在材料中,形式以神圣启示的形式出现,正如一位中世纪哲学家令人震惊的定理(由于这个定义,这位哲学家被当做异端)中所说,"心灵、上帝和材料是同一回事"(mens, Deus, et Yleidem sunt)。
我想得出结论——但事实上我们永远不可能得出结论,我们会放弃掉结论,好比贾科梅蒂放弃了自己的画作一样——在这个过程中,最具有风险的,但也最富有生命活力的,去重构出这部著作——像所有"创作中"的作品一样——让其继续永无止境地延续下去。
我指出了一个令人惊奇的事实,即重构本书的缘起和进展,必须与描绘出本雅明心目中的波德莱尔的诗歌形象携手并进——这样,所揭示的正是主题材料与让书成形的方式之间难分彼此。似乎是该书的生成过程——详细地展现了本书的架构的程式,我们在其中可以看到,书稿的形式正是来自于研究材料的蒙太奇拼贴(montaggio)——仿佛重述和摹仿了波德莱尔在与他的时代(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决斗中的策略。
对于一种震惊的经验——按照本雅明的说法,这种震惊的经验是波德莱尔诗歌的中心——在本雅明那里,对应的正是阿多诺或许很不恰当地称为材料的"令人震惊的蒙太奇"的东西,对于氛围(aura)消逝和恢复的诗性经验来说,在书中,它对应于研究者的一瞥,当他观看他耐心细致搜集的碎片时,他同时感到这些东西也观看着他,并成功地赋予这些碎片一种能力,即它们会返还他的一瞥——你们知道,这就是本雅明在第一次出版这本重要的碎片时,对氛围给出的定义。
本雅明——在国家图书馆的阅览室里,感受到他自己将这些书页发出的沙沙声,与画在穹顶拱门上的或者在巴黎街头闲逛中的树叶发出的声音混淆了,他试图去解码这个时代的暗号——本雅明面临着与波德莱尔与他的时代同样致命的搏斗。
我相信进入到本书迷宫中的读者——如果我真的说明这本书是"过程中"的作品,即在走向自己的途中的作品,它是活的作品,带有生命悸动的作品——最终会遇到一个怪异的怪兽:米诺陶(Minotaur),这个怪兽一半波德莱尔,一半本雅明,一半诗人,一半批评家。这肯定是最为神奇的经历——杂合的怪兽最终完美地对应于读者你们手中这本书的架构。这本书也是材料与形式、研究与成稿、阅读与写作的杂合体。
| Evernote helps you remember everything and get organized effortlessly. Download Evernot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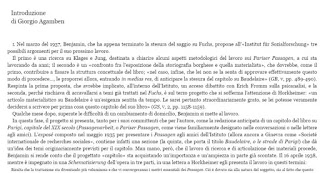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