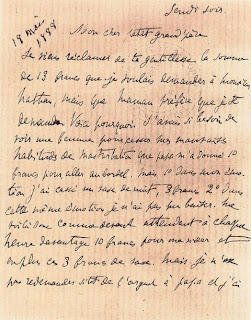http://www.lrb.co.uk/v36/n23/rivka-galchen/what-kind-of-funny-is-he
里夫卡•盖尔成
《卡夫卡:领悟的年代》作者:雷纳•斯塔克 翻译:雪莉•弗里希
我的结论是:任何人,只要花上足够长的时间来思考过卡夫卡,总不可避免地会发展出几个自已独有的看法来,这些观点虽说有点点傻气,可别人倒是别想掺和。(这些想法要是画成图,可能是抛物线形的,处于最高点的是那些花时思考最多的,和几乎不花时间思考而形成的观点。欢迎法律人士置疑)。我本人也有这样一个不成熟的想法:法兰兹•卡夫卡的一生读起来就象部真正伟大的喜剧。我这么说(这么所是自然而然的事)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卡夫卡本人生活里、生活外发生的那些悲剧,我之所这么说是秉承了喜剧一贯的传统,就象是理查德•柯蒂斯和憨豆先生的《黑爵士》里最后一节,在经过一节又一节的你亲我爱,你失我败,和异装癖之后,到1917年随着我们并不算英雄的人物们爬出了壕沟,倒向敌人那边而结束了整部剧。
卡夫卡的生活,至少是那些经历了时间还未曾被磨灭的部分里面有什么?雷纳•斯塔克以时间发展为序,写成一部接近2000页的卡夫卡传记,德语版三卷已出,现在第二卷与第三卷已经由雪莉•弗里希翻译成英文。(第一卷描写的是卡夫卡的青年时期,最后也已写成,卡夫卡生前最好的朋友麦克斯•布洛德现在的房子里有一个神秘的箱子,里面装满了文献,这所房子现在据说是布洛德情人的女儿(已年届七旬)所有,斯塔克以此第一卷希望这些文件能走出房子,大白于天下,但这些文件的归属权现在还有法律上的争议。)斯塔克的卡夫卡传记之所以会具有如此的吸引力,部分是因为他虽说自已也形成了很多已经得到事实充分证明的观点,但大多数时候他并没有在传记里表露出来。作者不愿意扩散性的作揣测、判定、和诠释,相反地对自己描述的对象有充分详实记录的生活,斯塔克愿意很谨慎地来记录他的点点滴滴。卡夫卡除了写过三部长篇小说,数不清的短篇小说,未佚失部分,短文以外,还留有日记,给朋友及家人的信,为受伤士兵事故预防和筹措资金呼吁作的演讲稿。到了生命的最终,即使是在做"静默治疗",他还是在小纸片上写下了基本的交流内容:"你有时间吗?有的话,请把牡丹花浇点水吧。"另一张纸条是写给爱着他,正照顾他的女人多拉•迪阿曼特的:"这样的日子你还能承受多久?你这样的承受,我看在眼里,我还能忍多久?"
反映真实情况的东西、真实的情况,与情感的,不可想象的、深刻的东西会在这部传记里齐头并进,次数多到经常可以与情感的诱发力互换。自传中讲到了卡夫卡这位年青的作家,保险公司的员工每天早上8:15会准时出现来上班;讲到他和最好的朋友布洛德一起住旅馆时,为了要不要关着窗户而把布洛德搞得不安生(卡夫卡胜了);讲到了在一家裸体主义者休养所的卡夫卡,是如何对两位年青瑞典女性的身体充满赞叹的;讲到了年轻的卡夫卡请求辞职去当兵;讲到他鼓励自己的父亲把钱投到一家石棉厂,后来厂赔钱,破产时又不愿意帮父亲经营,结果让他非常失望;传记里提到了卡夫卡有写过一个在石棉厂工作的女工;写他非常讨厌自己的父母晚上打一种叫franzefuss的扑克牌到很晚;写出版商把他的小说《在流放地》说叫成《在流氓地》,因为"流氓"这个词一出,书更有卖相。传记里写到卡夫卡央求他的姐姐奥塔出去买上二十本杂志,因为上面有登自己的小说《火夫》的捷克语译文;写到卡夫卡写信给他的翻译,他追求人家,可人家已经结了婚;有写到他写了一封长达16页纸的信,希望能得到《劳工意外保险局》的升职;有写到他在慕尼黑和诗人里尔克一起读诗,结果第二天的报纸上评他"表现得相当地差强人意";卡夫卡迫不急待地要写小说,可是有了两个星期的假期,他倒又是用来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他的父亲(这封信并没有给他),说他父亲吃饭太响,吃相太差,说他身形太过大,以至还是小孩子的卡夫卡和他一起去市立游泳池的时候,都会觉得自已又局促,又形愧;自传有写到他与人订婚,再解除婚约,再又订婚,后又解除婚约;写到他陷于了一个三角关系之中,这种事于他不是第一次了;写到了卡夫卡被诊断出患上了极其严重的肺结核,工作就没有了。我们在自传里看到卡夫卡收到了一封税务官的信,询问有关对布拉各第一石棉厂的出资情况,卡夫卡回信解释说工厂五年前就不复存在了,之后他又收到了一封信问他回信里并没有找到那个提到的原始信件,这么答复是什么意思,随后几个月后,卡夫卡收到了第三封信,威胁他说要是他坚持认为没有出资给布拉各第一石棉厂,那就会受到指控和罚款。自传里收有卡夫卡长达350页的对话用的希伯莱语的学习笔记;写有他临终前,和迪阿曼特晚上一起用手做皮影戏偶;有1924年临死前,这时的他虽已无法进食,还是最后一次校对了自己的短篇小说《饥饿艺术家》。
斯塔克清楚地表明,自己凭借真正"了解"卡夫卡的名义,做了这个传记工,里面肯定会产生相当的局限和不足。"把一个人的生活往回看,"他在序言中写到,"就象是个走到森林边缘的动物进了入视线,又会再次消失。"同时他也承认卡夫卡的生活和工作之间的和谐给人的启迪性是很少很少的。卡夫卡经常花上半天的时间就这么躺着,做白日梦,斯塔克认为这些别人无法进入的部分正是最重要的地方。可尽管如此,到这个程度上斯塔克所追寻的要为大家所知的卡夫卡,事无巨细要呈现的这个人,倒是提醒了我《一把尘土》里结尾的某些时刻,那个在巴西丛林里的文盲(Mr Todd),他爱查尔斯•狄更斯的作品爱到把书里的主人公托尼•拉斯特扣住不让走,要让他给自己读狄更斯一直读到死。有时候我在想要作个类比的话,斯塔克就是那个拉斯特,卡夫卡就是那个丛林里的文盲,有时候角色可能正相反:卡夫卡是那个丛林里的人,而斯塔克则是拉斯特。这部传记篇幅很长,所以我有时也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之后不久有些观点自己也会推翻,或是没有当初那么的强烈。以此,你晚接触到斯塔克的作品确实会带来影响---会同时伴有晚接触到卡夫卡的作品,只不过是各自的方式不同而已。
卡夫卡的作品要记住的就是其中的风趣,这话已经说了很多遍了。大家所知道的是卡夫卡把自己的作品大声读出来给朋友听的时候,自己会控制不住的笑,尽管在我理解这笑更多的象是一种焦虑而不是真有多高兴,但作品中风趣的地方还是历久弥新的。但卡夫卡是一种什么样的风趣呢:博尔赫斯说霍桑的小说《威克菲尔德》就是卡夫卡的前身,指出"主人公深入骨髓的浅薄琐碎与他超出常理的自我毁灭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里的观点有部分就是指不协调的比例问题---这是种喜剧天生就有的结构,一种与宇宙万物相关联的方式。这里我们可能不但会联想到《变形记》,还有《审判》里的那个请愿人,他花了一生的时间来等在"法门"外,这门就是为他而设的,可他永远都不得进。或我们可能会想到卡夫卡笔下的狗(或是他的猩猩,或是他的老鼠,或是四处凿穴的动物),那么慎重地对待自己的生命,就象个人似的真正地在解析自己的生活。
或是我们会想到真正严肃地对待生活的人,就像他们真也曾为过人似的。"很多的时候,我就怀疑自己是个人吗?"这时卡夫卡给自己的第一个求婚妻菲莉斯•布洛赫的纸条上写的,当时他正试图要解除婚约,但又不想自己先提出来,等着菲莉斯来提。"你要有足够的增重才可以结婚。"后来一个医生对患上肺结核的卡夫卡说,他怎么说总是不愿意结婚,或者是不想吃东西。如果我们观察的角度恰当的话,喜剧的尺度总是同时又是悲剧的尺度,正如卡夫卡在贺卡上写下的那些著名的话:"外面的世界太小,太过泾渭分明,太过真实,是不够容纳一个人内心的空间的。"
卡夫卡传记产生喜剧效果的一个元素就是他的生活无论在什么时候和他的作品一比都显得不那么重要。无论他是个有才华的作家,还是个尽心尽职的保险公司雇员,在布拉格一直住到了奥匈帝国走向末路,走进了20世纪20年代,卡夫卡是否符合你的想象,部分的原因要取决于你有多专注地紧跟校正性的文章、引言的每一节,另外还有你是否有这个能力能融入不同的声音,以及你对丰富的外部世界是如何看待。
如果在经过了很多年,读了这么多的卡夫卡,公众还是把它看成是和巴特比同性质的一类人---如果最能左右我们的是他要写成小说的毅力,或是他总是在谈鬼神,谈对一切都无法承受---那看不到:尽管卡夫卡是巴特比是同类,他同时也是巴特比那个本意很好,忧心忡忡,困惑不安的老板这一点倒似乎是难了。卡夫卡自己都觉得自己是个难搞的人。他在自己的日记里总是以第三人称来写自己,有一条他是这样写的:
他本应当安身于监狱了事。就当个罪犯来了此生----这可以是生命的目标。只是这监狱是个加了栓子的笼子。外面世界的喧嚣透过栓子不由分说,肆无忌惮地传进,传出,就如同在家里一样,所谓犯人其实并不曾被囚禁,他可以参与一切的事情,笼子外的一切事情都没有避开他,本来就很简单他可以离开牢笼了事,虽说有栓子,但离得都有几尺远,他根本就没有被囚禁。
因要不要到Georgental旅行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决定,卡夫卡居然感到了极大的恐惧,后来在一封给布洛德的信中,卡夫卡这样解释说:
对行将死亡,他有种极强的恐惧感,因为他还未曾活过。这么说倒不是说还没有过妻子,孩子,田地,牛群这些活着的必备品。生活唯一要必备的东西是放弃自命不凡,搬进一所房子,而不是赞美它,在房子周围挂什么花栏装饰。有人可能会说这是个宿命的问题,是不会交于人手控制的。可接下来为什么会有懊悔感呢?为什么这种懊悔感一直都在呢?是为了变得更精致,更美味?这也是要放弃的东西。但为什么这样的夜晚都是:我可以活着,我没有活着---以这样的论调结束的呢。第二个主要的原因是---可能真正只有一个原因,我好象是现在没本事把他们分得清----是这样一个想法:我视如儿戏的东西它真的就会发生。我的创作并没有把我带出困境。一生虽是漫长我并未活过,将来我真的会死。我的生活曾过得比别人甜蜜,我的死将会比别人的更痛苦。
布洛德回了信,基本的大意是他并不能真切地理解卡夫卡为什么这么抱怨。可事实上布洛德是以最重要的方式极其真切地理解卡夫卡的,不仅是当朋友还当成作家:正是他在卡夫卡有生之年主要负责了卡夫卡作品的出版,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卡夫卡的作品几乎都是多亏有了他。卡夫卡既有独特的才华又有让人厌烦的地方,这两点是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不可分的。
很多的时候他的个性会让人想到拉瑞•戴维和波蒂•沃斯特。很多卡夫卡定的计划,其方式都会引发计划最终的实现不成。五年的时间里,他和弗莉斯•鲍威尔谈恋爱,订婚,解除婚约,再订婚,但再解除婚约,俩人在一起的时间零零碎碎加起来不起过15天,就是这十五天也不总是开心的,(卡夫卡倒是写信追求弗莉斯的好朋友格莱特•布洛赫),卡夫卡在信里清楚地讲明,他是不能接受在婚姻里有性行为的。随后卡夫卡写了一封信给弗莉斯,约下次见面,到时有事要商量(因为弗里斯甚至还没有答应他的请求放弃工作搬到布拉各来),卡夫卡称弗莉斯是他的"人类法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卡夫卡不断地请求自己工作上的上司,同意他离职去当兵;但正如他后来在日记里写的,他并没有真走到这么远,当兵上前线;他永远是成不了一名士兵的。下一个他答应要娶的女性,以及再下一个他答应要娶的,卡夫卡都没有真正娶人家。写给父亲的那封长信他也没有寄出(或是毁了)。还有尽管他做了很详尽的规划,学了希伯莱语,他也没搬去巴勒斯坦。有时卡夫卡让他人很受折磨,他的方式有点类似于那个有着无穷魅力的堂吉诃德的所为,是对一种对不符合现实的,但更高贵的世界观的坚持。
从卡夫卡的这种行为模式里呈现的感觉是:这不只是从来不作任何承诺的人物---喜剧人物要来作承诺那这个系列喜剧就走到头了---还有这个人是多么的强大,还有他自己对这种强大的力量心里是多么矛盾。不论是对男人还是女人,卡夫卡引发起他们的爱意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密伦娜•杰森卡来询问翻译他作品的事,卡夫卡写信给她说:"你是我的。"尽管密伦娜开始是有些怀疑,便还是和别人一样很快对他有了回应。罗伯特•科洛普斯托克是卡夫卡在疗养院遇到的匈牙利医生,同样的也对卡夫卡有了爱幕之心,搬到了布拉各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成是为了靠近卡夫卡,可随后看到卡夫卡那样的避世,他倒是失望了。招人爱恋这种事,卡夫卡似乎是本人并不会刻意避免,他随后会觉得这爱恋让他透不气来,会要逃离。爱尔丝•伯格曼和丈夫一起移民到了耶路撒冷,她询问卡夫卡打不打算也去,卡夫卡写信回复到:"这趟行程要是和你一起前去,那必定会极大地增加这件事在精神上的罪恶性。不,我不能这样做,即使是我能这么做---我重复"所有的舱位都订滿"你来附和。"在这篇传记里卡夫卡并不是一个很性感的人物形象---事实上他也根本不是这样的人---但他明白只要有性掺与其中,会产生什么样的力量。就象他试图要一方面展现自己的魅力,另一方面又不想要这种魅力一样,他寻求的是那种貌似卑微的位置。
有时候他似乎是生活在一个情景喜剧里。到乡下去写作,他一开始觉得"景色很美,"可到了第二天又烦得写不下去了因为有小孩子在吹圆号,锯木场有叮噹叮当的声音,有快乐的孩童在外面玩耍,最后他忍不住大声叫到"你们怎么不去采蘑菇呀?"随后他发现这些孩子是邻居家的,这是个在当地磨坊里上班的工人,一直睡眠不好,工作又三班倒,回家打发七个孩子到外面玩,自己好睡一会儿。在治肺结核的疗养院里,卡夫卡和朋友科洛普斯托克对另一个住在这里的捷克高级军官开起了玩笑,这个人很爱众目睽睽之下吹笛子,到户外去写生画画什么的。军官搞了个自己的作品展。科洛普斯托克和卡夫卡俩人匿名对此写评论,一个以捷克语发表,一个以匈牙利语发表,受嘲弄的军官就跑到科洛普斯托克(因为发热呆在屋子里,卡夫卡在那儿陪他)那里还要他帮翻译那个匈牙利语的评论。经历了这次成功之后,卡夫卡又装神弄鬼发给他姐姐一个文章说什么爱因基坦的相对论为医治肺结核指明了方向。全家人都为这好消息高兴得不得了,卡夫卡不得不告诉他们实情好及时醒悟。
这些卡夫卡生活里的闲情趣事---其中很多都是差不多的类型---会让人立即有种既滑稽又充满了死亡,既有启发性又有晦涩难懂的感觉。我们不妨来问一问自己为什么我们可以去读卡夫卡作品的时候,还要去读他的传记做什么呢?你能读卡夫卡的时侯还要去做早餐做什么呢?你能读卡夫卡的时候还要去看电视,或是修指甲做什么呢?
我曾说过斯塔克所用的方法—他就象是《法网》里的那个Joe Friday,除了暗示研究生活就象是调查犯罪一样这一点以外,其它的只能说大抵是事实。尽管这部传记很详尽---我们从中知道了密伦娜的寄宿学校,知道了她父母的婚姻状况---斯塔克还是不得不省略了很多的东西。就纵是三卷部头的传记也不能穷尽其详,这就把斯塔克纳入进自传里的东西置于了一个不同的角度。尽管他总是三缄其口,不说自己的评论,但还是在传记里留出篇幅一一反驳了其它作家对日记里出名的那篇"1914年8月12日:德国对俄罗斯宣战。下午游了泳。"的看法。对卡夫卡给弗莉斯的信件,有更出名的评论----这个文献很容易被人解读或是误读成完全无视所写对象的长篇独白---斯塔克在传记中也挑出一些进行了反驳。在卡夫卡的性取向问题上,斯塔克并没有直接去谈那些什么卡夫卡可能更喜欢男性的暗示性的东西,他选择的是着重提到卡夫卡在日记中有简短地谈到对姐姐有性欲的感觉,而不是原文引用。对卡夫卡对男性肉体的观察,对自己倾慕的女性刻意要保持肉体上的距离,对男性间友情的强烈斯塔克只是记录,但并不在此作过多停留。(索尔•弗里德兰德的作品《弗兰兹•卡夫卡:耻辱与愧疚的诗人》在讲到这些话题就很机智,他没有用什么自作精明,确定的解释来给这些话题加上虚假的法码)可能比其它的传记作家,斯塔克在写卡夫卡的性取向上用到的篇幅要少---尽管他并不回避这件事,更多地时候似乎是在试图建立起卡夫卡是个异性恋的可信度,他不只一次地提到卡夫卡去过妓院--部分的原因是,在书中如果写到性取向,特别是什么乱伦,或是招孩子们喜欢等等这样的话,哪怕是一行,俩行都会产生误导,带来的影响是相当大的。
可能他只是想保护卡夫卡(这样一说我相信传记作家们日子要不好过了)。比方说传记才一开始,斯塔克就提及一部当代并不出名的波兰小说,竟然堂而皇之地想以一封卡夫卡的信来揣测他的内心,看得斯塔克把小说给撕了;看到这里我就觉得奇怪了,大多数传记作家,学者最多会把书撂一边吧。甚至还在序言里,斯塔克就开了一段,里面引用了一个18世纪德国讽刺作家乔治•克里斯托弗•李希腾贝尔格的一段比较晦涩的话,引用了只是为和他理论理论,还不是一处,二处的问题,序言之后在书中再也没提到李希腾贝尔格这个人。这些东西写到了传记里就显得相当的奇怪了,因为斯塔克,尽管书中还有用了很多不太出名的学术作品的,已经决定不去讨论沃尔特•本杰明有关卡夫卡的杂文,或是艾瑞克•塞特纳的那部让人敬重的作品了。要是以斯塔克为主角的话,那这部喜剧可就不好看了。大家来看看斯塔克对文人学者的那种Bernhardian式的简明扼要,他说这些人引用卡夫卡日记的有内容,"随意拆散,肢解,再重建,""完全是肆无忌惮,一般来说是以杂文的形式出现,以此作为自己在学术上进步的垫脚石。"这措辞可是有点过了,特别是因为有以研究卡夫卡混饭吃的人,他们以自己已有的作品为基础,再继续深入研究卡夫卡的作品再混饭吃,这么做也合情合理。斯塔克大多数的时候脾气还是温和的,只是到这种时候就没有了学者的相对理性,倒更象是一个非理性的父母似的。这就进一步给传记以一种悲怆的调子:随着书的一步步向前,斯塔克自己变成了一个越来越好的人物。
这种简慢式的敏锐描述越来越盛。他三言两语就把"卡夫卡风格"说成是某些地方含有"一种特别形式的浮夸,以分析的精准来混淆实际情况"。卡夫卡并不懂游泳,可有一个未佚失部分到是谈到了奥林匹克游泳比赛,对这样一个大跨越斯塔克说"卡夫卡并不要寻求什么形象,他已有自己的形象,只是因偱而已,他是宁愿不要自己的主题也不愿失去这种形象的合理性的,这一点就是他早期的读者就已经注意到了。"斯塔克强调说罪恶感和惩罚这些主题在卡夫卡后来的作品里出现得不那么多了。在卡夫卡日记后来的那些段落里---这个时候的他回过头来以第一人称而不是第三人称写自己---斯塔克注意到"相比于最容易预见了的颠沛流离,和悲观失望时卡夫卡发出的那么多哀叹之声,这个时候的他语调几乎可以说是平和的。"(举例来说,不管我的体质会糟到何种程度…我都要尽自己最大的力接受它,就我这样的状况,说什么这种病只有一种结束方法---这个方法就是死心---这只是空洞的诡辩)。在谈到《洞穴》---写于生命要结束时---斯塔克看到惊扰动物安静的那些神秘的声音:嘶嘶声,啼鸣声有规律的停着,这些动物们听到的声响是它们自己的生命之声,是它们的呼吸声;不住地惊扰天地万物之静默无声的是动物们自己,它们才是这份不安静的来源。"这样的观察很是细腻,但严格来说并非无懈可击,也不是特别的自传式的。可是这样的细腻,斯塔克大多数时候--并不是所有的时候—对这份细腻的抑制对整部书产生的影响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伟大的喜剧小说里,能产生喜剧的原素---往往都是社会规则,不论是这种规则是阶级的还是战争的---也是产生悲剧的原素,这话穆瑞尔•斯帕克在《人终有一死》,约瑟夫•希勒在《第22条军规》中都讲过。但在卡夫卡的生活里,这样的架构我们更要从与历史无关的角度来看,要放置到由卡夫尔自己经历世界的方式,他的个性造成的情形里来看。
很多喜剧小说中存在另一个喜剧原素,就是它们会拓展下来有一整套的小人物,这些人,无论他们的出场时间多么的短,凭借自身的风趣就会极深地抓住我们的情绪。斯塔克在传记里就是写活了很多精彩的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正是他们这部传记才会结束得如此出色,如此悲伤—或更确切地说,正是通过他们我们才感到了结局的悲伤,因为我们当然是早就知道了结局是这个样子的。尽管斯塔克对卡夫卡的姐姐奥拉,对他的翻译,相知最深的密友密伦娜等等她们的描写也特别的生动和相当有价值,可我所指的不单是,或者不主要是指那些起"主要作用的"小人物,比方说卡夫卡未婚妻们或是家庭成员们。有些小人物只占一段的样子,或有的甚至只有一两行。想想那个《22条军规》里的卡尔•穆勒,他在地方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叫《格雷格•萨姆萨的再次蜕变》的文章,文章说萨姆萨又活过来了,情况变得好转起来;可就在这文章发表之后不久,还很年青,很贫穷的穆勒就死于肺结核了。我们再来看作家奥斯卡•鲍姆,自打十一岁就眼瞎,为了支撑家庭教人钢琴课,卡夫卡的母亲写给他一封信,哀求他,作为一个卡夫卡圈子里一个已经结了婚的朋友帮卡夫卡"头脑清醒清醒"。从注脚里我们得知,鲍姆一生在出版商眼里不过只是个盲人专业文学编年史的记录者;他最应当被人记住,可并没有记住多长时间的作品是《通往不可实现之门》。我们看到一度曾受尊敬的作家约翰尼斯•施拉夫,已50岁,人已失常,还在讲毫无意义的什么宇宙,可他自己觉得高兴(在卡夫卡眼里是这样)呀。我们看到卡夫卡在劳工意外保险局的老板,他也会写诗,会很聪明地回绝员工要辞职入伍的请求,自己倒是最后死在前线。事实上劳工意外保险局的几个员工都会写诗,写小说。我们不是看到了在疗养院的那个乐呵呵的捷克人嘛,他想用一把镜子给卡夫卡看一下自己喉咙口的肿块,从来没有家人来看过他。年青的姑娘鲍尔,才只有18岁,从耶路撒冷出来旅行的途中路经布拉各,就当起了卡夫卡的希伯莱语老师。年轻,羞怯,懂礼的卡夫卡寄宿到了奥尔加•斯塔尔的旅店里,这们房东小姐把自己失败的订婚告诉了卡夫卡,卡夫卡则给了她看了自己手稿的长条校样。卡夫卡的姐夫一直运气不好,老是做生意失败。作家欧斯特•威斯非常讨厌卡夫卡,说他没有替自己的文章写简介。在植物园里一位可爱的还在上学的小女孩引起了卡夫卡的注意,因为她对着他叫着,卡夫卡微笑着,不断向他挥手,随后才意识到她说的是"犹太人"。
喜剧会让我们觉得安全,可能是因为其形式曾一度暗示着一会有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很难说《22 条军规》、《人总有一死》、或是《黑爵士》的结局就是皆大欢喜的。虽说事实证明我们一直读的都是鬼魂---这些我们已经知道了,但喜剧还是让我们把这一点忘记到足够长的时间,之后再让我们去记得。三卷长的传记,斯塔克写了三张纸长的序言,快速地讲到很多与卡夫卡的命运有过交结的人的命运。卡夫卡还活在我们心里;其它人则都已烟消云散,这是这部传记里最让人感动的部分。
| Evernote helps you remember everything and get organized effortlessly. Download Evernote. |